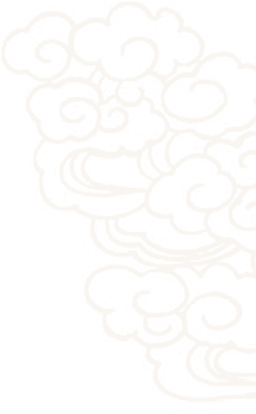人性回归与精神困境
——历史寓言话剧《兰陵王》论
王露霞
内容提要:历史寓言话剧《兰陵王》用现代寓言和写实相融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一个生活中的弱者,在羊性与狼性的挣扎中回归自我人性的艰难历程的描绘,深刻揭示了皇权文化对正常人性的碾压和浸淫,并且,在更高的层面上呈现了现代人本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
关 键 词:人性回归 精神困境 中国意象
近日,新编历史寓言话剧《兰陵王》在国家话剧院进行第四轮演出,该剧由罗怀臻编剧,王晓鹰执导,张浩越、夏力薪等出演剧中主要角色。剧作以北齐名将兰陵王的传奇故事为蓝本,用寓言和写实相融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一个生活中的弱者在羊性与狼性的挣扎中回归自我人性的艰难历程的描绘,揭示出人类生存普遍的精神困境,并由此传达出编导者澄明真相、渴求真情、探究真理的美学追求。以下作具体阐释。
一、羊性、狼性与人性回归
剧作通过讲述兰陵王的异化过程,对人性的两极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并由此对皇权文化的专制和残酷本质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批判。
(一)羊性的苟活与迷失:皇权对人性的碾压
兰陵王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慈母爱、健康茁壮成长。但某一天,当一位道貌岸然、凶险狡诈之人,阴谋将其父杀害,并将其母占为己有之后,他天堂般的生活大厦便倾塌了。那时他仅仅九岁,一个本该天真浪漫的年龄,却被无助、恐惧和绝望所笼罩。为了生存,甚至为了活命,他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伤痛,投其所好地取悦皇权,以获得苟活的机会。这是一个弱者无奈的选择,尤其是他男扮女装,粉面柔态,极尽所能地献媚于齐主时,观众的心在滴血!
但是,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长期扮演某一角色后,或者说他无力改变自己的角色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在潜意识中形成对这一角色的认可,从最初被动的扮演到最后主动的顺从,从而导致自我人性的迷失。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共同弱点。如果说初受迫害时兰陵王还持有反抗与复仇的意念,那么,当“可人儿”的角色暂时减缓了他生命危机,或者说,“可人儿”的角色使他暂时获得皇权的“恩宠”时,他便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虽然他也有所反抗,但他的反抗是微弱的、消极的、不明方向的本能抵抗。所以,当齐主以皇权威严逼迫他“让出”心爱的姑娘郑儿时,他纵有诸多的不舍和眷恋,但在权力面前还是放弃了她。如果说我们看到他以媚态侍弄皇权而哀其不幸,那么,此刻更加怒其不争。这是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普通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形象,剧作家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揭示了皇权文化对正常人性从躯体到精神的无情碾压,从而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劣根文化最尖锐的批判。
(二)狼性的残暴与冷酷:人性的自大与张狂
对普通的个体而言,往往具有双重人格:谦卑与狂妄。无论是谦卑还是狂妄都是正常心理的扭曲,是对正常人性的戕害。剧中的兰陵王便是如此。剧中第一折,当齐主欲争夺郑儿时与兰陵王有几句对白:
齐 主:兰陵王!
兰陵王:臣在。
齐 主:可人儿!
兰陵王:陛下……
这一对话经演员的逼真表演非常耐人寻味:当齐主把兰陵王作为一个正常人而唤他为“兰陵王”时,他可以挺胸抬头正视齐主;可是当齐主把他作为一个“宠物”而唤他为“可人儿”时,他立刻消失了锐气,本能地屈就下来。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后面的“大面”在剧中有着同样的叙事功能。当兰陵王站在阴森空旷的庙宇之下,面对先王神圣威武的雕像,他意识深处的英雄情结也渐渐泛起,他有着对血性男人的本能渴望,说明他没有彻底地沉沦和迷失,这也是他后来之所以还有可能回归正常人性的必要前提。尤其是兰陵王与先王的空中对话,更加促使他由一个柔弱弄臣向一个真正男人的转变。在这里,与其说是先王的声音和幻影,倒不如说就是兰陵王心底那颗不甘、不死的灵魂,呼唤着作为弄臣的、麻木的兰陵王。
然而,回归真正的男儿本色谈何容易!如果说从昏睡中被唤醒是人性回归的第一步,那么,醒来后的路如何走才更重要。剧中兰陵王遵从先王的指引:“带上大面,找回英雄的尊严!”那么,何为英雄的尊严?带上大面就一定能找回英雄的尊严吗?客观地讲,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仅仅表达先王或者说就是兰陵王本人一种内心的渴望。父亲的大面,仅仅赋予了他一种外在的形式。当然,尽管只是形式,仍给予他巨大的、积极的心理暗示:他顿时神情亢奋、热血沸腾!他顿时手持长剑,英武威严!此时的兰陵王就像身着娇艳女儿装便相信自己天生应该女儿身一样,相信自己是王者。尤其当命运赋予他领军打仗的机遇时,他英武善战的本性使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但是也很快被胜利和权力冲昏了头,短暂的自信很快转变为自负和狂妄,最终在处理俘虏问题时便表现出狼性的残忍和冷酷!
从根本上讲,长期的粉面女妆,长期的被豢养和蹂躏已经极大地挫伤了他的生命意志和人性尊严,使他长期处于一种自卑和压抑的精神状态之中。所以,一旦拥有了权力和荣誉,他的思维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面对失败的军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杀!”他太想证明自己的“王者”身份了,他太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供人玩弄的宠臣了。于是,他以草菅无辜的生命为手段,企图洗刷自己多年遭受的欺凌与屈辱,企图找回自己男儿的英雄本色。不成想,他的行为却走向意愿的反面,成为一个杀人成性的魔鬼,某种意义上,成为他所憎恨的另一个“齐主”。剧作真实地揭示了兰陵王在拥有了权力和荣誉之后的自负与张狂,并由此导致的残暴、冷酷的“狼”性心理。
与兰陵王的“狼”性心理相呼应,剧作也成功塑造了齐主的“狼”性形象。齐主与兰陵王可以说是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共同呈现出在皇权文化浸淫下人性张狂、自负的丑陋,以及残忍、冷酷、自私、贪婪的狼性本质。由此可见,皇权文化对正常人性的碾压不仅仅表现在躯体和精神方面,它甚至已经渗透到灵魂深处,浸淫到骨髓血液中,成为无处不在的幽灵,在潜意识里左右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可以说话剧《兰陵王》对皇权文化的批判,已经超越国界,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批判。
(三)人性的回归:母爱对灵魂的拯救
话剧《兰陵王》另一特征是赋予了人物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这一成长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充满屈辱的,甚至是以牺牲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剧作才获得了充盈的戏剧性张力,具有极高的悲剧审美价值。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与《兰陵王》,在戏剧结构和人物关系上具有同构性,而其人物性格、命运走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复仇的梦想,哈姆雷特始终是清醒的,尽管他以疯癫的外表作掩饰。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剖析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过失,这对于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
相比之下,兰陵王虽然有对美好爱情的追寻、对身处逆境的反抗、对英雄情结的崇拜,但一旦面对强权威慑和内心绝望,所有的美好和反抗便烟消云散。当然,兰陵王对自己的行为也有反省和忏悔:郑儿为其牺牲生命时,他的真情流露尽管常常被其冷漠的外表所掩盖,但在不经意间也渐渐融化着他内心的怨恨和伤痛。但是,一旦回到现实,他又固执地返回冷漠,固执地让仇恨所包裹、所缠绕。可以说,兰陵王头上的面具是他心灵面具的外化,如果心灵的情结打不开,他头上的大面将永远无法摘下。剧作在此使用了一个象征“预设”:若想卸下大面,除非最亲最爱的人用她心上流出的血,方能将之融化。于是,母亲为了让兰陵王明了自己才是他最亲最爱的人——实际上,母亲是为了唤醒兰陵王的正常人性,让他回归到一个既具有勇武胆识又具有悲悯情怀的成熟男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此刻,母亲拔下针簪,刺进心房,鲜血浇注大面。舞台上,经灯光、音乐和舞美的巧妙设计,刹那间整个舞台被“鲜血”所笼罩,浓重、强烈的色彩冲击,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剧作的悲剧力量也在次迸发!不仅极度渲染了母爱的光辉,更是她灵魂的一次彻底的洗礼与升华。
而沐浴在母爱光辉中的兰陵王同时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和生命的涅槃:母亲的鲜血不仅融化掉他头上的面具,更重要的是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或者说,正是母亲的鲜血打开了他灵魂的枷锁,他头上的面具才自然地得以脱落。他幡然醒悟,怀抱母亲,进行了深刻而虔诚的反省和忏悔:“母亲用她的一腔热血,再次给予我新生,她只要我相信,世间还有爱,世间还有情……兰陵王愿从此做个有爱有情有义之人……”至此,那个自私、冷酷、狂妄的兰陵王死去,一个敢于承认错误,一个在羊性与狼性挣扎中,不再沉沦、勇于奋起,不再迷失、勇于担当,并拥有了悲悯情怀和真正男人气概的兰陵王诞生!中国有句古话,称“浪子回头金不换”,与哈姆雷特的醒悟相比,回过头来的浪子兰陵王的人性回归便具有了独特的中国理念、中国情感和中国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凤凰涅槃”。
话剧《兰陵王》用无私伟大的母爱,把兰陵王从弄臣的羊性和凶残的狼性双重错位中引领到正常的自我人性中来——既具有丰沛强悍的生命膂力,又具有聪明高贵的理性智慧和悲悯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怀臻的追求是完整的,超越了之前单纯对生命强力的追寻,更加自觉地将视点聚焦在赋有感性与理性完美融合的人物身上,从而为中国当代戏剧贡献了又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兰陵王。
二、中国元素与现代寓言
正如导演王晓鹰所言,他企图以此剧来践行自己“中国意象的现代表达”的创作理念。在这部剧作中,我们的确体察到了编导的良苦用心和收到的显著效果。故事本身以及叙事手段都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比如,剧作讲述的就是北齐武成帝高湛奸嫂屠侄的故事,主人公兰陵王在历史上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外,舞台上“百戏”的展示,《兰陵王入阵曲》经典音乐与舞蹈的应用,以及传统剧目《杀宫》的经典片段,面具入戏本身也是古典“傩戏”的一种表演方式。如此之多的中国古典元素的加入,使这部作品具有了追溯中国艺术源头、展现中国艺术魅力的韵味和特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开拓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对话剧艺术的中国化和民族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然,故事和符号的使用仅仅是一种手段,最终所指向的是“现代表达”。那么,这部作品表达了什么?如标题所示:“历史寓言剧”,也就是说,它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怎样的现代意识?杰姆逊说:“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 〔1〕(p.118)话剧《兰陵王》就是一部具有某些寓言性质的作品。依照杰姆逊的观点,《兰陵王》具有多重阐释空间,并且这样的多重阐释有时是相悖的,这给解读带来一定的难度。以笔者的一面之见,这部作品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孤独感、漂泊感和荒诞感,从而呈现出现代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
(一)个体生命的孤独感
“孤独感”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存感觉。自从尼采声称“上帝死了”之后,人的内心变得无比空虚。现代人生活在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里,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之中,经历着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时刻。这种孤独感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寻找的主题。话剧《兰陵王》便是对这种寻找的接续,而充溢在剧作中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使剧作具有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审美力量。
兰陵王对母亲刻意的回避和冷漠,源于在他九岁时亲眼目睹了如今的齐主杀死了他的父亲,而他的母亲又很快委身于齐主身边做了皇后。这不仅令他恐惧,更令他心寒和绝望。从兰陵王来讲,与丧父之痛相比,母亲的背叛更令他难以承受。他所有对美好世界的信念顷刻崩塌:跟父亲那么恩爱的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竟那么顺从地与仇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最美好、最坚固的感情还这么不堪一击,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和追寻的呢?由于自己无力与这个极权世界抗衡,只能这样自贱自弃、毫无尊严地苟活,而对母亲的怨恨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开始他企图忘记儿时与父母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对母亲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冷漠,后来又刻意忤逆母亲的意愿,以及在作践自己的同时实施对母亲从身体到精神的屡屡伤害。待到他亲手杀死了齐主报了杀父之仇,母亲以及众大臣向他澄明了当年事变的真相之后,他仍然不肯理解和原谅母亲。对于母亲多年来的隐忍、对他时时处处的呵护、对他怒其不争的伤心和忧虑,以及整个过程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他却拒绝接受!如果说羔羊时期的兰陵王因不明真相而迷惘和自甘堕落,那么,带上英雄面具的兰陵王因不肯相信和接受真相,内心同样是迷惘和空虚的。儿时的心理创伤使他变得多疑和冷漠,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人即是地狱”。所以,他始终生活在封闭的小天地里舔舐、咀嚼自己内心的伤痛,在他那些偏执几近癫狂的行为背后,潜伏着巨大的恐惧和孤独。
剧作在第一折最后一段:兰陵王惶惶无措,眼睁睁地看着郑儿被人带走,硕大、空旷的宫廷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痛苦地倒在地上欲哭无泪!忧伤与失落、绝望与虚无之感,几乎将兰陵王“零落成泥碾作尘”!而宫廷的硕大空旷与人物的卑微渺小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此时此刻,舞台配以戏剧音乐的雄浑、低沉,配以灯光、音响的电闪雷鸣,所有这些将整个舞台那苍凉、悲怆、茫然无助而又难以言说的情绪推到极致,个体生命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二)个体生存的荒诞感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荒诞感是从对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为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2〕(p.190)中国当代艺术对荒诞的呈现,主要来自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性模拟,而话剧《兰陵王》对荒诞意识的把握却别有一番韵致。剧作家把荒诞的存在作为人性的两极来呈现,在生活的具体情境里有意识地造成真实与虚构、身份与行为之间的错位,来凸现个体生存的荒诞性。
首先是兰陵王的男儿身与女儿妆、王子身份与宠臣形象的错位构成的反讽效果所生发出来的荒诞感。兰陵王本是一位王子,英武俊朗,其父更是一代天骄,万众敬仰。兰陵王本该秉承英雄世家的血性,但为了活命,必须投主子所好地扮成女妆,成为十足的宠臣,尽管内心有所抵抗,但仍在不断沉沦。不仅伶人们绘声绘色地讥讽他的妆颜,就连他自己也迷失在所扮演的角色里无法自拔。此刻为命运所迫,人物的真实身份与其行为之间构成巨大的反差,个体生存的荒诞性在此彰显。
其次,头戴面具的兰陵王的威猛外表与其羸弱、空虚的内心构成的落差所生发的荒诞感。戴上先王大面的兰陵王虽然找回了一些自信,但长期的被压抑和蹂躏使他仅有的一点自信很快转变成自负和狂妄,为了洗雪昔日被人玩弄的耻辱,他不惜以牺牲无辜的生命为代价。实际上,只有内心空虚和缺乏自信的人才不断地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而且草菅人命让他的内心陷入更大的虚无。所以,在他威猛、张狂的外表下,遮掩的是一颗更加怯懦、空虚、孤独和迷茫的内心。此刻,舞台上,在对兰陵王排山倒海的欢呼声里,在兰陵王志得意满的狂笑声里,人物命运的荒诞感由此迸发。
当然,在话剧《兰陵王》中,“荒诞”既是揭示人类本真生存状态的一个主题,又是剧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独特手法,是他对现实生存深刻而独到的内心体验外化成的一种叙事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反讽”“戏谑”的叙事手法,但它是一种更具写作难度和美学精神的叙述,因为剧作家骨子里依然是严肃的。
(三)个体灵魂的漂泊感
作为最个人化的内心体验,灵魂的漂泊感始终充溢在话剧《兰陵王》中,构成人物最本真、最刻骨的生命体验。大幕开启,郑儿有一段内心独白,而这段独白明确地道出了其漂泊无依的精神状态:“天涯任我行,何处是归程?”为了追寻灵魂的自由,她独自漂泊在三山五岳之间,她的内心始终有一个声音回旋:“我是过客!长安的过客,江湖的过客,人生的过客。”当遇到兰陵王的时候,她以为她有了归宿,不料,迫于权力,他很快放弃了她。至死她没能一睹兰陵王的真正面目,但她的内心始终怀有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因此,她对“家园”的寻找异常浪漫而充满乌托邦想象。
兰陵王的无根漂泊感更是显而易见。整个剧作都是他寻找本真自我的过程。他不断地发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但由于长期的苟活与迷失、战争胜利后的自负与狂妄,他没能真正地了解别人,也没能真正地返视自己。后来,在生死存亡的一刹那,郑儿用年轻的身躯挡住了来自仇敌的那把尖刀,可以说正是郑儿的死亡之“光”撬开了他尘封已久的灵魂冰点。最后,更是母亲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他蛰伏已久的正常人性。剧作在想象中通过个体生命的良知与觉悟达到了社会化的和潜意识的满足。
三、西方舞台手段与中国舞台经验
话剧《兰陵王》虽然叙述的是中国故事,表达的却是现代人共通的精神困境,所以,在叙事手法上既借鉴了诸多西方舞台手段,又有中国舞台经验的呈现,使整个剧作看起来既意蕴丰厚又大气磅礴、既亮点纷呈又浑然一体。
(一)内心独白的使用
内心独白是一种人物心灵的自我对话,能够摈弃对外在世界的防范和伪装,更容易逼近内心世界的真实情状,包括那些不可为外人道的隐情和伤痛。话剧《兰陵王》使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比如伶官在金碧辉煌的神武宫的内心独白,道尽了皇宫的骄奢淫逸、浮华奢靡以及帝王将相的丑态和荒诞。类似的独白随处可是。这些独白省去了大量场景的设置和人物之间繁琐的对话,更简洁明快地直抵事实的真相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剧作中还出现了更耐人寻味的内心独白。比如在“楔子”开头部分,兰陵王吟哦着诗句素服走上,另一表演区郑儿走上。此时,两人分设在两个表演区,分别进行各自的内心独白,但他们独白时都在望着对方,而且独白的内容都与对方有关。某种意义上,这应该算作两人之间的对白,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白,有一种既说给对方又说给自己听的意蕴。再比如,在第一折,兰陵王极尽妩媚地取悦齐主,齐主满场追逐兰陵王,此时兰陵王的内心独白:
看见了么,这便是大齐国的当朝皇帝,难怪后世史家将我北齐称作禽兽王朝……据说后世史家考证,兰陵王有父无母。生母无从稽考,兰陵王的母亲成了千古之谜……
这样的独白已经涉及到叙事视角的变化问题。叙述者似乎站在当今时代回望北朝时期所发生的故事,而不再是主人公本人站在当时当地的立场。这里有一个人物、叙述者和作者位置互换的现象。这在现代叙事学上是一种常见的叙事手法,但运用到戏剧独白中便显得灵动而韵致迭出,有一种陌生化的美感。
(二)戏中戏的多层次表达
话剧《兰陵王》为了揭示齐主谋杀先王的真相,以中国古代偶戏的表演形式,以经典传统戏《杀宫》剧情为基本故事框架,通过三次不同细节和情节的展演,来揭示不同的人物,为了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视角所得出的不同的结论。那么,何谓事实真相?或者说,你以为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就是事实的真相吗?当然,在本剧中,通过前后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谋杀事件的真相可谓不言自明。但是作者运用戏中戏的艺术形式,把同一个故事通过不同的情节设置,呈现出不同结论这样一种构思和展演,不仅使剧情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极富戏剧性美感,更重要的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比较深奥的哲学命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三)简洁明快、蕴涵丰厚的诗性语言
话剧《兰陵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诗性语言的运用。它的诗性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语言的韵律感上,更表现在言词内部所蕴含的丰沛的韵致和深刻的哲思上,而且简洁明快。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富有丰富的潜台词。
舞台上,诗性意象也是诗性语言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些意象撷取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诸多元素,又将其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形成气韵生动、超象空灵又充满无言暗示的诗性空间。比如,多功能的简约钢构穹顶,贯穿剧作始终。它在接通传统戏曲的“写意之美”与现代工艺的“质感之美”的同时,更有一种权力与威严的象征。或者说,它悬置天际,就是皇权的符号化,芸芸众生皆在它的统治之下;再比如,神兽大面和傩舞,既是剧情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生发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仪式感。这种建构在中国传统艺术符号基础之上的整体性舞台意象,不仅与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刻画契合无间,具有极强的视听形象冲击力和戏剧性情感的感染力,同时又蕴涵浓郁的寓言特征和诗性哲思,是话剧舞台上的一种诗性意象或诗性语言。由此,剧作对话剧舞台语言空间的开拓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也产生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综上,话剧《兰陵王》通过饱蘸诗性语汇的舞台意象、内心独白和人物对话,深刻批判了皇权文化对人性的碾压和异化,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人个体存在的精神困境,表达了澄明真相、渴慕真情、追寻真理的道德操守和艺术理想。
参考文献:
〔1〕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该文已发表于《东方艺术•东方鉴评》